体育博彩,在线体育博彩,线上体育投注,最佳体育赔率,体育,体育博彩平台推荐,正规博彩平台,体育投注平台,体育投注app,体育博彩平台网址大全,体育博彩平台,体育投注平台推荐,靠谱的体育投注平台,体育投注靠谱吗,线上体育投注平台推荐,线上体育投注平台,体育博彩加密货币网站,体育赛马投注,体育投注平台大多数学者亨廷顿将世界简单划分为7个或8个截然不同“文明”的做法。尽管他的框架确实过于简化,甚至其吸引力也恰恰来自这种看似明确的划分,但学界对亨廷顿理论的全盘否定,最终扼杀了关于文化如何塑造国际关系与经济发展等议题的严肃规范性讨论。不同文化间的断层线究竟在哪里?哪些文化能真正推进其公众利益的发展?国家在阐释与捍卫民族文化认同方面应扮演何种角色?对于那些渴望获得终身教职的学者而言,整个这一领域都变成了不敢轻易碰触的禁区。
“西方文明史”课程的式微实则已持续多年,且愈演愈烈。早在上述华盛顿会议召开的10年前,此类课程在美国高校中的主导地位便开始遭遇线年代,一系列的社会动荡让很多人开始质疑:我们被灌输和教授的历史,到底是谁的历史?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这些课程“有些是自然消亡的,有些则是被直接扼杀的”。以斯坦福大学为例,在二战结束后的许多年里,“西方文明史”一直是该校的一门必修课。学生们可以通过阅读该课程推荐的一系列经典著作,了解到远至柏拉图和卢梭,近到马克思和阿伦特等人的思想和观点。

在许多批评者看来,像“西方文明史”这类如此宏大的课程,却只能从浩如烟海的经典著作中择取寥寥数本纳入其中,仅凭这种在编纂教材时所暗含的明显随意性,便足以成为废止该课程的理由。“我们为什么只选柏拉图,却不选亚里士多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主任约瑟夫·图斯曼在196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质问道,“为何不多选些欧里庇得斯的作品?选了《失乐园》,却又为何漏掉但丁?有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为什么没有马克思?”
这些关于编纂的争议固然激烈,但却掩盖了“经典之争”所暴露的更深层问题,以及这一争论背后的重大意义。几十年来,这类通识课程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实则基于如下前提:美国的学术界和高校学生需要将自己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并将美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同欧洲乃至古代的历史渊源相联系。正如19世纪90年代美国历史学会的某位评审委员会成员所言:“若脱离了欧洲历史的根基,美国历史不过是一只悬浮于半空的气球。”然而,拴着这只气球的绳线如今却被割断。
许多人曾主张彻底摒弃“西方”这一概念。在他们眼中,即便存在关于“西方”一词的定义,那也是不完善且嬗变的,而它同帝国主义的强权、种族优越感,以及殖民地压迫之间过于密切的历史联系,更进一步瓦解了其描述力。例如,夸梅·安东尼·阿皮亚就主张抛弃“西方文明的概念”,因为在他看来,这一概念“往好了说是众多混乱的根源”,而“往坏了说则是阻碍我们应对当今时代重大政治挑战的绊脚石”。对阿皮亚等批评者而言,“西方”已经成为他们道德谴责的对象,因为它既阻碍了对历史的认知,又以繁复的叙事架构加重了历史解释的负担,其遮蔽之功远胜启蒙之效。他们认为,这座思想大厦必须被全面推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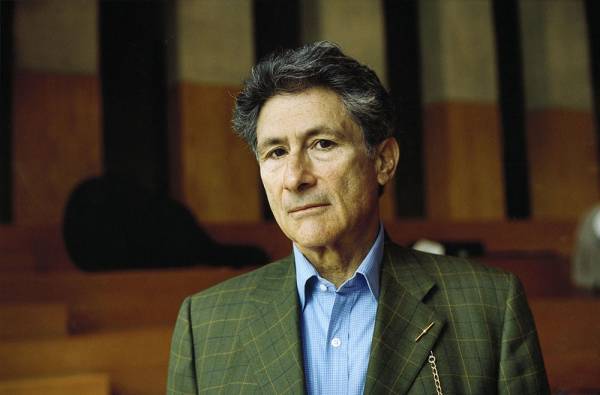
这部著作也重塑了美国乃至全球人文院系的学术机制与内部政治格局。作家潘卡吉·米什拉曾写道,《东方学》“催生了上千个学术职业生涯”。的确,该书在美国高等教育界催生出一个新的“产业”,其核心任务就是瓦解对世界的殖民主义式理解。但米什拉同时指出,这部作品也为某些“以男性为主的知识分子移民”提供了一种获取晋升的路径。而讽刺的是,这些人“往往原本就是其国家的统治阶级成员,甚至来自殖民统治时期的得势阶层”。正如米什拉所言:“对于某些高种姓的东方人而言,谴责东方主义的西方已然成为其在西方谋取终身教职的终南捷径。”
《东方学》对文化领域的改造如此彻底且全面,以至于今天的许多人,尤其是那些硅谷精英,几乎意识不到它在塑造和构建当代话语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未曾想到其对自身世界观所产生的影响。蒂莫西·布伦南在《萨义德传》中写道,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后殖民研究不再仅仅是一个学术领域”,而是演变成了一整套包含“‘他者’‘杂糅性’‘差异’‘欧洲中心主义’”等高度特定化术语的世界观,而且现如今,这些术语“在剧院节目单、出版社书目、博物馆导览册乃至好莱坞电影中都随处可见”。
他的核心论点,即言说者的身份与其所言说的内容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已成为当代人文学科中众多基础性内容的前提。这种对“言说者与言说内容”“叙事者与叙事”乃至“身份与真理”关系的认知重构,带来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在某些极端的表述中,它也带来了负面效应。正是对其核心主张的过度延伸,催生并助长了解构主义运动的兴盛。在随后的数十年间,这场运动最终将言说者身份的重要性,抬升至超出言说内容本身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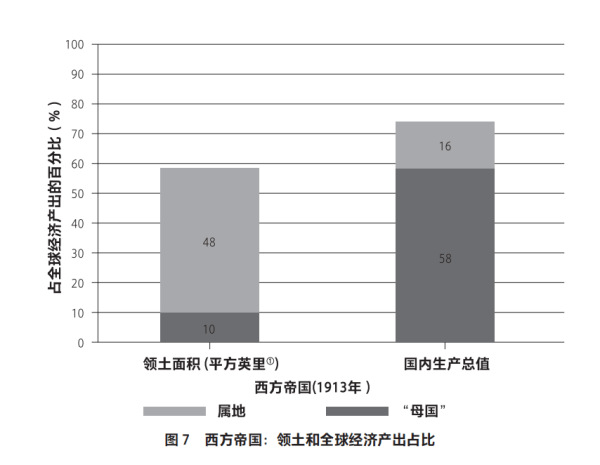
在20世纪下半叶,对“西方”及其历史和认同的系统性挑战,连同对美国使命过去为何、理应为何,乃至其是否真实存在的质疑,最终导致出现了一片思想真空。旧有知识体系的瓦解或许情有可原,但至今却仍未有任何新体系出现并取而代之。这场始于20世纪60年代大学校园、后被称为“经典之争”的论战,以及随后学术界对“西方”这一概念本身的质疑,不仅是一场关于“美国认同之内涵”的争论,更是一场“美国认同是否应有任何内涵”之争。
然而,在美国及许多其他国家,对国家的归属感正在逐渐被简化为某种狭隘且不完整之物,比如那些仅靠共同的语言或娱乐、体育及时尚等流行文化来建立的松散联系。鼓吹这种趋势的也不乏其人。到20世纪70年代末,整整一代人已对更广泛的国家认同或共同事业产生了怀疑。而正是这一代人,包括很多后来创立硅谷并推动计算机革命的先驱,开始将目光转向个体消费者等领域。当国家使命及其存在理由都已遭到彻底质疑时,这些人对推动政府的种种“冒险行为”也渐失兴趣。
